

骨科 李云飛:在草原曼巴的感召下
8月30日下午,虹橋國(guó)際機(jī)場(chǎng)大廳內(nèi),一條“生命曙光,健康希望”的紅色大標(biāo)語(yǔ)赫然醒目。來(lái)自全市12家醫(yī)療單位的21名醫(yī)療人員組成的志愿者醫(yī)療隊(duì),在市衛(wèi)生計(jì)生委副主任鄭錦的帶領(lǐng)下整裝待發(fā),即將開(kāi)啟為期6天的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西部行公益診療活動(dòng)。而我有幸成為了其中一員,隨隊(duì)開(kāi)赴祖國(guó)的大西北。
甘南藏族自治州是全國(guó)十個(gè)藏族自治州之一,地處青藏高原東北邊緣,南與四川阿壩州相連,距甘肅省省會(huì)蘭州450公里。全州總面積4.5萬(wàn)平方公里,境內(nèi)大部分地區(qū)海拔在3000米以上。我們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自治州西南部的瑪曲縣,那里平均海拔3460米,年均氣溫2.3℃。瑪曲,系藏語(yǔ)“黃河”之意,因比鄰黃河而得名。區(qū)域內(nèi)人口88%為藏族,是純牧業(yè)區(qū)。
在上海,還是一身夏裝的我們,到達(dá)蘭州時(shí),已經(jīng)需要加一件外套避寒了。隨著一路上海拔高度的不斷刷新,氣溫也越來(lái)越低,到了中途的碌曲,車(chē)外甚至已經(jīng)飄起了鵝毛大雪。到達(dá)瑪曲已是清晨時(shí)分,同行的隊(duì)員,已有不少人穿上了厚厚的羽絨服。然而,高原之上最大的困難并不是寒冷的天氣,而是稀薄的氧氣,很多志愿者來(lái)到瑪曲后的幾天,均出現(xiàn)了頭痛、心率加快、失眠等缺氧癥狀。就算是平日里身體素質(zhì)尚佳的我,也出現(xiàn)了高原反應(yīng),稍微加快點(diǎn)步伐,便開(kāi)始上氣不接下氣了。一上午的義診下來(lái),由于要反復(fù)與藏民們溝通交流,缺氧癥狀便愈加明顯了,嘴唇發(fā)紫,頭暈?zāi)垦#氲阶约贺?zé)任在身,稍作休息調(diào)整后,便又重新投入了工作。
瑪曲地處藏區(qū),藏民的生活素來(lái)是逐水草而遷徙,牧民都是住在帳篷里面,濕冷的環(huán)境,加上不良的衛(wèi)生習(xí)慣,導(dǎo)致各類(lèi)關(guān)節(jié)炎癥和感染性疾病患病率極高。盡管這里的醫(yī)院都是由政府全額撥款,但是因?yàn)獒t(yī)療條件實(shí)在太差,根本留不住人才,整整一個(gè)外科系統(tǒng)卻只有三名醫(yī)生,連僅剩的一名負(fù)責(zé)骨科疾病的醫(yī)生,后來(lái)也跳槽到了州里。有一次,義診結(jié)束后,我們正在會(huì)議室休息,一名當(dāng)?shù)氐奈骞倏漆t(yī)生急匆匆地找到我。原來(lái),有一位橈骨小頭脫位的患兒家屬,看到了上海醫(yī)生公益診療的宣傳掛圖,于是聞?dòng)嵍鴣?lái)。橈骨小頭脫位對(duì)于骨科醫(yī)生來(lái)說(shuō)是個(gè)很簡(jiǎn)單的病例,當(dāng)孩子很快被治愈,高興地?fù)]舞著小手時(shí),家屬不停地向我道謝。后來(lái)我得知,由于瑪曲人民醫(yī)院沒(méi)有骨科醫(yī)生,外科醫(yī)生又不會(huì),以往類(lèi)似這樣的疾病都要驅(qū)車(chē)2-3小時(shí)趕到附近的臨夏縣,甚至趕到州府合作去求診。當(dāng)聽(tīng)到這些,我的心不禁揪了一下。
貧乏的醫(yī)療資源,不僅導(dǎo)致了當(dāng)?shù)氐陌傩盏貌坏胶芎玫尼t(yī)療服務(wù),醫(yī)療人員也因常年得不到進(jìn)修學(xué)習(xí),理論基礎(chǔ)和臨床實(shí)踐能力都比較差。授人以魚(yú)不如授人以漁。我們此行的目的,不光是幫助當(dāng)?shù)匕傩战鉀Q一些現(xiàn)有的疾病問(wèn)題,更重要的是,要把先進(jìn)的醫(yī)療技術(shù)和水平傳授給這里的醫(yī)生,讓這里的百姓長(zhǎng)期受益。盡管由于時(shí)間的限制,我們并不能將所有的知識(shí)和技能傾囊相授,但至少,我們可以針對(duì)某一類(lèi)疾病進(jìn)行耐心、細(xì)致的講解和分析,竭盡我們的全力,幫助他們有所提高。
來(lái)到瑪曲后,我終于見(jiàn)到了2010年感動(dòng)中國(guó)人物之一的王萬(wàn)青,正是在他大愛(ài)無(wú)私的精神感召下,西部行公益診療活動(dòng)才走進(jìn)了瑪曲。1968年,王萬(wàn)青從上海第一醫(yī)學(xué)院畢業(yè)后,主動(dòng)請(qǐng)纓來(lái)到了條件艱苦的甘南藏族自治州瑪曲縣工作。42年來(lái),他多次放棄回上海的機(jī)會(huì),憑著對(duì)藏族同胞的深厚感情,克服生活、語(yǔ)言等種種困難,全心全意為牧民解除病痛。在阿萬(wàn)倉(cāng)衛(wèi)生院工作的20余年間,他累計(jì)接診7萬(wàn)余人次、手術(shù)上萬(wàn)例,他讓全鄉(xiāng)3000余牧民擁有了自己的健康檔案。來(lái)到瑪曲縣人民醫(yī)院后,他開(kāi)展的多項(xiàng)手術(shù)填補(bǔ)了瑪曲高原外科手術(shù)空白。為了更好地預(yù)防控制高原疾病,他與藏族妻子起早貪黑,逐一給當(dāng)?shù)啬撩駥?shí)施預(yù)防接種。他刻苦鉆研,翻譯醫(yī)學(xué)資料10萬(wàn)余字,在國(guó)家級(jí)和地方醫(yī)學(xué)雜志上發(fā)表科研論文20余篇。退休后,他依然給上門(mén)求醫(yī)的藏族群眾治病送藥,還經(jīng)常指導(dǎo)縣醫(yī)院的外科手術(shù),被當(dāng)?shù)厝罕娪H切地稱(chēng)為“草原曼巴”(藏語(yǔ),漢語(yǔ)譯為草原醫(yī)生)。當(dāng)我們驅(qū)車(chē)來(lái)到王萬(wàn)青老先生最初工作的阿萬(wàn)倉(cāng)衛(wèi)生院,看到那里的簡(jiǎn)陋條件時(shí),不得不對(duì)王老先生心生欽佩。也不得不感嘆,在中國(guó)幅員遼闊的土地上,不同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水平的區(qū)域要保證醫(yī)療資源的合理分配、醫(yī)療工作的良好開(kāi)展依然還是個(gè)大問(wèn)題。能否在人性化和法律的制度化之間取得相對(duì)的平衡,仍是需要深入研究和不懈努力的。
通過(guò)這次公益診療活動(dòng),我在反復(fù)思考自己的人生觀和價(jià)值觀,取舍之間,我更加明白了“生命所系,健康所托”的深刻內(nèi)涵。也許,王萬(wàn)青老先生只是這個(gè)時(shí)代的產(chǎn)物,但是他對(duì)社會(huì)、對(duì)群眾這份責(zé)無(wú)旁貸的使命感,卻是每個(gè)救死扶傷的醫(yī)務(wù)人員,應(yīng)該堅(jiān)守并付諸行動(dòng)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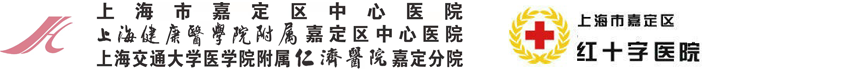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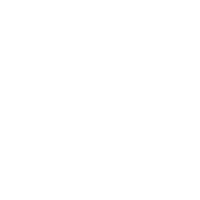




 滬公網(wǎng)安備 31011402005736 號(hào)
滬公網(wǎng)安備 31011402005736 號(hào)